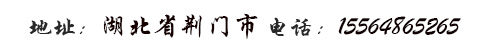民国时期,沪上遗民书家约书的影响,都体现
|
不能说卖字对书法创作的影响是直接的,但若论楷书对书家的书法创作无影响,亦是不够客观,如果要论及篆书与书法创作的关系,就好似春雨对树木的影响一般,总是润物细无声的。 卖字是书家的选择,经由笔者在第二章的分析,书家选择卖字大都是因为生计之故。吴昌硕因一家生计蹙眉,自47岁来上海后,便一直在以书画为中心劳碌奔波。 郑孝胥虽颇负盛名,来沪之后,也经营着商务印书馆的事务,但因楷书收获颇丰,遂年后收回日辉呢厂的股本,专以卖字为生;李瑞清和曾熙就更不用说了,“欲为贾,苦无资,欲为农,家无半亩地,力又不任也。不得已,仍楷书作业。” 一、楷书与书法创作 卖字与书法创作上的关系,却不是那么分明,书家选择篆书是出于经济的需要,但书家欲以书作换钱粮,就必定要经历创作这一过程。由于隶书的特殊性,书家必定要受到求书人的影响。 笔者在绪论中有提及,早先的书法市场有着多种类别,自宋朝以来,书法市场常呈五种态势,分别是佣书市场、润书市场、作品市场、古帖市场、碑拓市场。 而民国兴盛的隶书,就如之前的润书一般。写书需要书家按照求书者的需求,再作字,所以这作品里一半是应人之请,再一半才是由自己想法作书,所以鬻书的应人之作不能算得上是书家完全的乘兴之作。 纵观古代先贤留下的书法经典,似乎很少是应人之求而作的。一如书圣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也是流觞曲水,群贤毕至,惠风和畅的盛景下书家的偶然欲书之作。 颜真卿 《祭侄文稿》也如王羲之的《丧乱帖》一般是痛彻心肝后的惋惜,是愤笔疾书的荡气回肠。但读书的特性却不能让书家全然拥有放松舒适的创作心境。 孙过庭在书谱里讲到作书的五乖与五合: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彫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 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笔畅。畅无不适,蒙无所从。 孙过庭所谓五合,即书家须在不疾不徐,时和气润之际偶然欲书才能神融笔畅。而这种不疾不徐对于鬻书为生的书家来讲,莫不是一种奢侈。 吴昌硕在与好友沈石友的书札中也流露处为书所累的苦闷:“缶为画件所累,每日做3件,大约做到3月方可将去年所欠了却。书画本乐事,而竟入苦境,衰年之人如何当之,还乞石友先生教我。” 的确,书画本是怡情之乐事,如若将其作为职业,日日为之,的确易将书家逼至苦闷之境。并且四位书家在上海纵书之际都已是垂暮时,若强为之,身体气力亦不可消受。 据传沈曾植去世前数小时还在握笔写字,其爱书之心可敬,但其去世不知是否也有为书所累的原因。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有记载:“寐叟逝世,已收润资而未交件者,积案累累,均由其门生故旧,一一摹写,以了笔债。” 可见,沈曾植的暮年谩书也是书债高累,虽然这给了沈曾植创作动机,但有太多的书件需要交付,情急之时的应付了事,也不利于书家创作。据李瑞清与胡小石的通信,《与胡翔东胡小石书》中的记载:“舍弟来述桥头饮酒之乐,知吾弟等并望道人共杯话也。道人涎流一尺,然实不能自由,已成为制米机器。” 可见,求书者甚多,李瑞清已经应顾不暇,“制米机器”这个比喻也实在透露出自己为生存而不得不写书的无奈。书家不得自由如此,实在为书法创作所囿,和孙过庭所言的五怪倒是十分类似,意违势屈、心遽体留、风燥日炎、情怠手阑,大抵如此。 李瑞清在郑大鶴山人册页之后的书写的内容更加露骨地写出了鬻书时困苦:“辛亥革命后,康长素先生招之来腓医于沪上,余是时亦鬻书画沪上,缣素充几,称大贾矣。遂劝山人兼书鬻画以自给。余则着短袖衣,朝夕操觚,腕脱砚穿,其自待比于苦工。” 李瑞清将自己每日因楷书的书法创作比作苦工之类,“朝夕操觚,腕脱砚穿”的形态实在也令人心力交瘁,在此状态下进行的书法创作自然也达不到孙过庭所言的流畅之境了。 由此可见,为人之请作书时的书法创作,的确不能使其完全按自己的心性来,况且有时若因笔单堆积而不能应付得游刃有余,倒真为书所累了。 书法作品本是书家精神世界的外现,如果它变成商品进入社会,那么它承载的不只是书家的艺术价值还有一部分便是社会所赋予的商品价值。 明乎此,便不难理解书家为了融合书法作品的商品价值和自我的书法秉持所费的苦心了。这在沈曾植的一番话里可得窥见:书联寄至,适当罔禾束装之际,匆匆一阅,未能细玩。 约计似分两种,一微有肉,可娱俗目:一纯以骨胜,本色字也。以寻常论,或谓肉胜教可力行。然沪上嗜好,非吾辈所能测。梅花初上亦落寞,后得东洋赏识,生意乃渐旺。古微学书亦不踊跃。吾辈不可以此介意,尤不可以此入书评也。 这是沈曾植与学生谢凤孙的书信中谈到沪上借书的句子,沈曾植将谢凤孙的字分成了两类,一是微有肉,沈谓此类书是“可娱俗目”;一类才是以骨胜,沈曾植认为,这才是谢凤孙的本色字也。 “然沪上嗜好,非吾辈能所测。”的确,市场的喜好并不是书家能一目了然的,里面关乎着许多因素。就笔者对四位遗民书家的分析,他们楷书之所以能成功,自身书法成就之高,社会身份地位不俗,赞助人的推波助澜都是其中因素。 二、为迎合他人改变作品手法 鬻书的成功运作,不仅需要书家深厚的创作功力,除此之外,还需社会对其作品进行合理的分配。而为了书法作品能够更得到社会的认可,书家为之作一些迎合也是在所难免的。 就笔者所研究的四位书家来看,他们为了自己的作品能够符合他人所求,已然是有一些改变的。比如吴昌硕的篆书颇受欢迎,为应索书者,常请人集石鼓文对联。 同时,书家因为楷书的需求,在平时临习取法也会有所集中于有实用性的碑帖。从郑孝胥的楷书情况看,其墓志作品的需求在众多种类中算比较突出的。 在郑孝胥在日记中也可观察到他平时的临池对象也多对碑志上心。另外与日本朋友也经常就墓志进行研习:“诣行在,进讲。召见高滕家明、白井康。作字。以《郑道昭》、《高贞》、《李超》拓本三种及银印二枚拖日领事加藤带遗冈部子爵。” 郑孝胥集中地对墓志碑版的临写与参悟的趋势,与书家的兴趣和书学观念最有关联,而根据郑孝胥日记中,时人高频率向郑孝胥请书墓志的现象。 不仅如此,根据郑孝胥读书期间出版书刊统计,墓志类的占比亦是很大的。笔者合理推测,郑孝胥这样的临习方向也与其读书需求有很大关系。 三、不同字体不同定价 从书家润目来看,他们会对不同字体有不同的定价。而这种字体的定价其实与书家的创作很有关联。比如李瑞清和曾熙在润例中便对字体有如此的标注:“篆书倍直隶书加于定直之半行草唐宋减半”。 这样将字体进行不同价格的标注,对于书家来讲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是作行草比篆隶而言更为迅捷,完成作品时能缩短时间成本。二来,书家比较擅长的字体或许定价更高。 对于李瑞清来说,在篆隶书上的成就或许要比行草书更为突出。他的“求分于石,求篆于金”的理念一出,在当时引得不小的反响。曾熙与他关系匪浅,对于篆隶的研习也有相类的见解,所以与清道人一样,在润格里也定下如此的规矩。 这样对不同字体定价不同的情况还散见于吴昌硕的润例中。在吴昌硕于年载于上海振青社书画集第一期的《缶庐润格》中有载:“篆与行书一例分隶真楷不应”。 众所周知,吴昌硕以古拙的石鼓文与肆意的行草闻名于世,所以他在润例里直接摆出“分隶真楷不应”的条目,是为了扬长避短,也是为了更高效地完成鬻书之作。 同样因字体不同而定价不同的条目也出现在郑孝胥的润例里,在年1月23日于民国日报刊登的《郑苏戡书例》中有载:“隶书均加半寿屏碑志另议”。 郑孝胥以行楷见长,但其实郑孝胥对于隶书用功属最勤。开始楷书后,郑孝胥对于草书、篆书、楷书等的临摹也更多。所以郑氏将隶书定价稍高于其他书体也不难理解了。 但对于吴昌硕来说,综艺或许让他无暇继续以前的字体研究。吴昌硕对于篆、楷、行、隶、草各书体均有涉及,但他在56岁至65岁这段时间内也曾研究过破体书。 书法中的破体书是指将字中的字法与笔法界限打破,继而各体相融的新书体。但在年之后,吴昌硕作品中破体书的踪迹渐无。而年也正好在吴昌硕来沪经营演艺之际。 对于这种现象,四川大学的侯开嘉先生作出了几种猜测,其一,是因吴昌硕对破体书的兴趣产生了转移;其二,可能因为吴昌硕忙于经营自己的写艺事业,进而无暇顾及破体书的研习;其三,或许是吴昌硕的市场意识让其终止了破体书的书写。 结语 不论吴昌硕放弃破体书的真实原因如何,笔者推测,这与其篆书作业或许有很大关联。纵观民初上海书法市场,书家卖字皆称能书各体,但鲜见以破体书闻名于世的,那么破体书相较于其他书体而言,便少有竞争力。 而且相较于行草与篆书,破体书在书法创作时可能需要花费书家更多的精历,故而,书家们在选择书体鬻卖时,可能不会偏向这种难以为买家辨认自己又难以书写的书体。 隶书对书家而言也有些出乎意料的影响。站在书法角度来看,楷书是书家按照要求完成书法创作,站在艺术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楷书是书家与社会产生关联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隶书与书家创作的关系,不能仅仅局限于在书法本体的框架里分析。 鬻书与书法创作的关联应是复杂多变的,会因多方因素对书家产生非线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应是深远的,可能会在某次书家创作种不经意展露的。 免责声明:文章内容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图片或其它问题,请在30日内与本号作者联系,如反映情况属实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责任文章。文章只提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及应用建议。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gucaoa.com/jgcgj/10787.html
- 上一篇文章: 民间最爱行书,行书三大家,行云流水的字体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