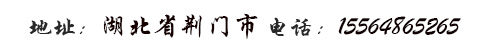吕金光于洁论黄庭坚禅宗心性论及其书学
|
北京皮炎医院哪些好 http://pf.39.net/bdfyy/bdfzj/210410/8833134.html黄庭坚画像 摘要: 黄庭坚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其禅宗核心是追求“心性”、“顿悟”,且孕育着“脱俗”、“重韵”的美学思想。黄庭坚的书学思想及艺术观点深受禅宗中悟道思维的影响,这是在“韵”的文艺观下所体现的一种“脱俗”思想,并始终贯穿于他的艺术领域中,包括审美思想、艺术理论和创作实践。显然,“脱俗”成为黄庭坚美学思想的重要核心。 关键词: 禅宗思想;书学思想;脱俗;韵胜;美学思想 隋唐之际,禅宗以其简易清新的姿态脱颖而出,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广泛推崇。禅宗削繁为简,使佛教徒从繁琐教条、苛难戒律中解脱出来,并与儒家的“以孝悌为人之本”的理说相契合,使佛儒两家根源上的分歧得到缓解。唐末的安史之乱给南宗提供了有力的契机。由于有朝廷的支持和褒奖,南宗的崛起有了政治上的庇护并逐渐成为正统。到唐末五代,禅宗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系统,步入了“五家七宗”的新阶段。 北宋禅宗以心性论为精髓,通过对心性的修养和升华,追求个性的解放、心灵的自由与真情的自然流露,抒发自身的意境和情感,因其符合当时士大夫阶层追求自我的审美取向而逐渐深入人心。所以以禅入诗、以禅入画、以禅入书、以禅应景成为宋代文人所倡导的时代风尚。 黄庭坚书法《苏轼黄州寒食诗跋》一 禅宗的影响在宋代文人黄庭坚的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黄庭坚自幼受其祖母仙源县君的熏陶开始接触禅宗,中年即皈依禅宗①。自小就广泛涉猎佛典为他奠定了深厚的佛学理论基础,并且与当时一些著名的禅师如云门宗的法秀、觉海、佛印禅师;临济宗道臻、仲仁禅师,黄龙派祖心、悟新、惟清禅师;杨岐派在纯禅师等来往密切②。黄庭坚受临济宗黄龙派的影响较大,南宋释普济所编的《五灯会元》卷十七将黄庭坚视为黄龙心禅师之法嗣。 黄庭坚对禅宗的吸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南宗直指“心性”,直表“本心”的悟道方式,使其做到了“养性绝俗”的自身品格修养。禅宗的重要宗旨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③。这种不做表面功夫、反观内心、明心见性的思维贯穿于黄庭坚的整个思想修养中,其强调学习要靠内心灵光贯注,以心灵统帅学问,反求本心中修养自身的不俗人格。 禅宗讲“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庄子讲“退听返闻”,孟子讲“反身而诚”、“反求诸己”,都融合为宋儒向内用功的修养论。④直观地引用禅语并在此基础上得到“心性”、“本心”的自我诠释,形成了自身修养的积淀,可见黄庭坚不仅能吸取禅学思想,而且能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与思维方式中。黄庭坚在《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中写道: 虚心观万物,险易极变态。皮毛剥落尽,唯有真实在。 其中的禅理表现得十分清晰,以“心观万物”则能看到其真实客观的一面。这造就了黄庭坚萧散自然、简远脱透、不拘于法度的个人风格。黄庭坚以心性论为奠基,通过心性修养获得内在升华,超越现实和生命的痛苦,摆脱烦恼,以达到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 进一步地说,黄庭坚追求的是自然天成、返璞归真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他所追求与崇尚的理想境界。是一种融合自然、以自然为友的律动美,是士大夫修身养性的方式①。事实上,也是黄庭坚所谓的书学思想上的“韵胜”之意境。 黄庭坚追求自然、寻求本真的思想同样是受禅学的影响。禅宗认为可从山川河流、草木丛林、鸟语花香等万物自然现象中悟解禅理。这些远离世间嘈杂、幽僻静寂的空间既充满着蓬勃盎然的生机,又孕育着自然适意、清净恬淡的禅意,让人身心融合,抛却杂念和纷争,达到“本心”、“真心”。 翠竹黄花非外境,白云明月露全真。头头尽是吾家物,信手拈来不是尘。② 离离春草,分明泄露天机;历历杜鹃,尽是普门境界。③ 大自然中的事物无一不体现着佛性,不加修饰的渲染才能得到了悟,触物即真。禅宗善于引导从大自然的陶冶中获得开悟,无迷狂式的冲动和激情,有的是细微、幽深、玄远的清雅乐趣和一份宁静、纯净的喜悦。从“翠竹”、“黄花”“白云”、“明月”、“春草”、“杜鹃”中参透禅机,开悟本真,追求豁达洒脱的胸襟气度,崇高恬适的人格境界。 黄庭坚受禅学影响颇深,善于在大自然的山水笔墨之间参禅悟道: “月落庵前梦未回,松间无限鸟声催。莫言春色无人赏,野菜花开蝶也来。”(《晚起》) “静中与世不相关,草木无情亦自闲。挽石枕头眠落叶,更无魂梦到人间。”(《眠石》) 他将自己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从大自然中得出自己的心性感悟,进一步地反馈于自然。从“无人赏”、“蝶也来”、“亦自闲”、“到人间”中享受其乐趣、禅悟其奥妙,从禅家思想中透视出淡然忘世、超尘脱俗之审美追求和随遇而安、乐观旷达之精神格调。并且将平实悠远、妙对人生的感悟展现在其诗文中,造就了其安闲恬静、平淡自然、虚融淡泊的独特艺术风格。从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到禅宗的渗透,使其审美趣味更加平实化、自然化。 尤其在人生低潮时黄庭坚阐发了许多超尘出世之想,在禅理中领悟、寻求解脱苦难的人生哲理: 风生高竹凉,雨送新荷气。鱼游悟世网,鸟语入禅味。(《又答斌老病愈遣闷》) 黄庭坚深受禅宗的影响,在自然中寻找到思维的依托,将其饱满畅达的感受融入艺术创作中,他善于发现和展示生活中的美,追求洒脱无碍、圆融自然的审美趣味,在世间纷扰中寻觅到清静、脱俗的个人情趣,进而创造出充满韵味且怡然自得的艺术境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韵致。他从禅宗真正了悟人生,也实现了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其老师苏轼就称赞道:“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答黄鲁直书》) 黄庭坚从自然现象中了悟禅理、明心见性、触物即真,面对旷寂的宇宙、静谧的自然,抒发出自身淡淡的情思,化作自然适意的闲适之情,艺术审美情趣也潜移默化地向着静寂旷达、平淡幽远、忘却物我的方向发展。表现在他的创作中则呈现出一种情景交融、浑然天成的意境美,达到平易自然、飘逸空灵的艺术之美。 第二个方面,黄庭坚吸收了禅宗思想中的“顿悟”思想。禅宗与其他佛教宗派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禅宗不提倡苦行僧般的念经拜佛,强调只要心中存在佛,不必过分地追求外界的坐禅苦修,即顿悟“心性”,开悟“本心”,则能“立地成佛”。他在《跋唐道人编余草稿》中道: 意大利著名作家卡洛·科洛迪创作的童话《木偶奇遇记》中,老木匠雕刻了一个能说会笑的小木偶——匹诺曹。每当匹诺曹说了谎,他的鼻子就会变长。故事最后,匹诺曹在历险中经受住了重重考验,最终成为了一个诚实、勤劳、善良的孩子。 黄庭坚将禅宗的“顿悟”很准确地运用到其书法中,不外乎其行、草书都是长枪大戟,是从“群丁拔棹”中“顿悟”出来的,从而才能达到“意之所到”即“韵胜”的境界。其《书自作草后》中也有其“顿悟”的融入: 绍圣甲戌,在黄龙山中,忽得草书三昧。② 即是其办理母丧后居乡时所题,其中不乏佛教用语“三昧”,意指心情平静,不受杂念滋扰,这是佛教重要的修行方法之一。这里借指“顿悟”到学习草书的要领,得其精髓。黄庭坚对自然景物做禅式的思考,抛开外在的束缚,进入物我相忘的境界,然后在纸上放纵笔墨,幻化出凝练的线条、如痴如梦的意境。这种具有真性、变幻意味的墨戏,便是在灵感到来时刻的“顿悟”。黄峪还认为“顿悟”的前提是“胸无尘俗而富万卷,广博精深可逢源”。即“顿悟”是“胸有万卷”所使然。黄峪之所以崇尚杜甫、韩愈的诗和文章,是因为其“不俗”。他们的创作之所以不俗是因为其中没有一字无来历,当然,这是学养和读书的结果。黄庭坚称赞嵇康诗“豪壮清丽”,称许苏轼黄州时作品“语意高妙”,这无不与他们胸无尘俗而富万卷,具有崇高的精神世界和深厚的学养有关。笔下尘俗者,是“读书未精熟”所至;笔下无尘俗者,则是“胸有万卷书”所然。黄庭坚的“顿悟”不仅是瞬间的悟道,更是自我修养的沉淀,读书精熟的积累。他一身儒林正气,一生以治心修性为宗本,即“养心”,达到“心斋”的精神状态,终于使自己在养性绝俗中不断丰富自己、完善自己,成为一个学养丰厚、风节修养超拔的人。黄庭坚很贴切地通过“顿悟心性”得出“韵味”、“不俗”,这在他的书法中同样得以很好的体现,他不断从禅宗中汲取营养,并融入到他的书法中,诠释出一种静谧的境界。这是对生活的描绘、对道的领悟,在去尘绝俗中不断地推动着禅宗的“艺术化”与书法的“世俗化”的结合,最终在“尚韵”中达到了禅宗与书法的一脉性。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二 在禅宗为主体的艺术观指导下,黄庭坚的书学思想以重韵、脱俗为核心,重“韵”成为黄氏书学的思想灵魂。他以禅宗的美学思想及审美标准阐述其书学思想。山谷云:“书画以韵为主。”③又云:“笔墨各系其人工拙,要须其韵胜耳。病在此处,笔墨虽工,终不近也。”④在此之前无人提出“韵”是书法审美的主要标准,山谷明确地把“韵”作为书法审美范畴并加以追求,他是第一个以“韵”作为审美标准进行书法批评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他评苏东坡书法“笔圆而韵胜”,“虽用笔太丰而韵有余,于今为天下第一”,“虽有笔不到处,亦韵胜也”。显然,他把禅宗之“心性韵”化为书学之“尙韵”,即要求书法超越工拙法度的束缚,追求真实的自我意志:“字外有字,境生象外,在有限的笔墨线条组合中,表现出丰富、无限的艺术创造者的情感意趣和精神追求,给观赏者以取之不尽的联想和启迪。”⑤只有这样的书法作品,才是有“韵”的思想境界。“韵”成为他书法审美的标准,而取“韵”、求“韵”则成为他的书法审美理想精神与追求。 由此,黄庭坚认为二王之书法,之所以“韵胜”,不在于技法的娴熟,而在于“右军笔法,如孟子言性,庄周谈自然”。将禅宗融入到书法艺术中,以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体现出晋人的风度和所谓的尚“韵”之情性。黄庭坚言: 然山谷在黔中时字多随意曲折,意到笔不到。及来棘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① 余尝以右军父子比之文章,右军似左氏,大令似庄周也。由晋以来,难得脱然都无风尘气似二王者,唯颜鲁公、杨少师仿佛大令尔。① 明确指出了其颜鲁公、杨少师的渊源是由于“似二王”、“仿佛大令尔”;是由于“无风尘气”即“不俗”、“韵胜”。颜、杨不仅取法“二王”,并且得到蕴藏其中的宝藏——“韵胜”。他这种重书法之“韵”显然与禅宗从魏晋玄学汲取营养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旨在以禅韵论人韵,以人韵论书韵,通过书法提升人格精神。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山谷之前的书法美学思想中,虽然曾经有过不少关于书法神采及主体精神方面的言论,如王僧虔的“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②;孙过庭的“心手会归,若同源而异派”③。还有张怀瓘的“状貌显而易明,风神隐而难辨”④等等,但从来没有人阐述过主体与客体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审美范畴,没有在理论上论述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自觉。而黄庭坚的“韵”正是一个有本体意义上的美学范畴。正如黄君先生所言: “它不仅完整地统一了书法主、客体的关系,而且第一次明确地把它作为书法艺术最高审美标准提出来的。”⑤ 山谷在具体运用“韵”作为对书法审美评判标准之时,不再是以形式、技巧、功力和法度为标准,而是以作品中的内涵意蕴及书法家所表现的情感、意趣和个性风采为准。由此,在创作中要臻于这一点,应通过练笔,对法度、技巧和功力的积累转化为“炼心”。其实就是强调书家的人格修养与学识胸次。这相较于他的禅学之审美而言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三 在书法方面如何能达到“韵胜”与“不俗”呢?黄庭坚认为,书法家首先要有高雅不俗的人格,他曾在《书缯卷后》指出: 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为少年言,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老夫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平居终日,如含瓦石,临事一筹不画,此不俗人也。⑥ 强调学书之人,要“胸中有道义”,并“广以圣哲之学”、“灵府有程政”、“临大节而不可夺”,要有孤傲自守、不随世俗的人格境界,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具有崇高意境与独具个性的书法作品。否则,即使书法的功力不减钟元常、王逸少,但“灵府无程政”,人格低俗者,也只能称得上书匠,而不能创造出内蕴丰富而独特的精神价值和表现力的书法作品。其实,“不俗”和“有韵”在主体精神涵盖上是相通的,所不同的只是层次与范畴各有侧重。“不俗”作为一种审美取向,应该从属于“韵”这个范畴。如王著、周越、李建中等人之书法是“乏韵”,即是“俗气”;苏东坡、杨凝式等人的书法“韵胜”,即是“无一点俗气”等等⑦。 刘熙载关于“俗气”和“韵”是这样阐述的: 黄山谷论书最重一“韵”字,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言“韵”也。⑧ 黄庭坚在《题王观复书后》说: 此书虽未极工,要是无秋毫俗气。盖其人胸中块磊,不随俗低昂,故能若是。今世人字字得古法而俗气可掬者,又何足贵哉。⑨ 由此可见,黄庭坚强调艺术家要有高雅不俗的人格修养,仍然是由“韵胜”的审美理想的艺术追求所决定的。这也是禅宗中的“顿悟本心”在书法中的真实写照。 黄庭坚的“脱俗”正得益于此修养论。其呈现予世人一种超然脱俗的姿态,这在其书法创作实践中表现极为鲜明。其最能表达感情的草书用笔衔接处连贯较少,但其错落穿插丰富、线条凝练、以静制动,与之前草书大家的癫狂迥异,使得鉴赏者无不被其心境所折服。不得不说这与其禅宗的自我修养、追求本真、崇尚韵论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禅学思想在黄庭坚题跋中处处可寻: 予尝评书:“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至右军书,如《涅般经》说伊字具三眼也。此事要须人自体会得,不可见立论便兴诤也。① 其次,书法家要有丰富的学养与情趣。如苏东坡言之,“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②也就是说要提高书法自身的精神境界及艺术表现力,必须丰富书家的文化学养。黄庭坚认为,苏东坡的书法不仅技巧、法度方面无可指责,而且能韵高意胜,这不仅是人格力量的作用,还在于他有着丰富而全面的文化修养,并将这种学问修养融入了自己的性情。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③ 苏轼胸中的学问、文章、“书卷气”,构成了书法艺术表现的内容和特色。强调要读书、有学问,才能丰富书家的才情,滋润书法家的心灵。诚然,在伸纸落墨时,便书中有意,兴致盎然,意出法生,得无法之法,在笔墨形质以外,构筑一种灵奇,其实就是脱俗。他在《跋周子发贴》中是这样说的: 王著临《兰亭序》、《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字》,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④ 虽然,王著、周越的书法功力深厚,技法娴熟绝妙,极善用笔,但其书法却不能脱尘出俗,根源就在于缺少字外的修养,即学问修养。因此,随世碌碌,即寡于见识,又乏于情趣,最终不能致妙于心。这一观点与他的禅学观点不谋而合:“心能转腕,手能转笔,书字便能随意”。⑤ 由此可见,学问、才情,是升华书法艺术文化品格和医治“俗书”的最佳医方。 值得注意的是,黄庭坚在关于“不俗”的观点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他的“创新”之说,即“自成一家之说”。他“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观点对书法的发展影响极大。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尽管有唐一代名家各自具有鲜明的个性,在张怀瓘的倡导下,唐人把“与众同者俗物,与众异者奇才,书法亦然”作为一种创作思想,但并没有达到对个性追求的时代共识。这对唐代来说,无疑是一种悲哀。而黄氏把追求个人风格,强调个性,避免与古今书家雷同纳入书法本体“意”、“韵”的视野,这在书学史上算是一个创举,这与他吸收禅宗中的追求本真是息息相关的。他说:“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⑥他又引汉人杜周“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以为律,后王所是以为令”⑦的话论证变法创新是自然法则。他始终以超轶绝尘为抱道自居,处处为自成家法之创新者称颂,不遗余力地宣扬创新精神。最终使“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艺术主张,强烈地影响了整个书坛。尤其是在当时的书风陈陈相因,人人争相摹习晋唐法帖的情况下,“法”严重成了人们的桎梏,“脱俗”创新的呐喊可谓一针见血,深深地“刺痛”了整个书坛,使之觉悟与惊醒,并为整个书坛普遍接受,成为中国书学思想中一个永恒的共识。但黄庭坚主张“创新”和“自成一家”,绝没有轻视技法和传统之意,而是在理解并把握前代书家精神实质后的自我发挥与超越,是技进乎道的升华。正如他在《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中言之: 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① 显然,这与他的禅宗观点完全相同,即主张师法,又“不为牛后”,力倡新变,自成一家,臻于崇高的艺术境界,即意在无弦,平淡而山高水深。可见,一家之法既是无法之法,也是自由之法。 四 由于黄庭坚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使其文艺观念形成了“脱俗”、“韵胜”的美学思想,其形成因素多是方面的。 首先,从历史层面讲,宋王朝极富改革精神。哲学思想上,理学分宗立派;绘画上,文人画日渐成熟;文学上,宋词取代唐诗为主导;书法上,“尚意”为主导,力破陈法,使书法面貌大大改观。这对黄庭坚来说,无疑是形成“脱俗”、“重韵”的时代环境。 其次,受交友之影响,黄庭坚深受禅宗中黄龙派的影响。随晦堂祖心禅师修行,与同门道友悟新、惟清交游甚好。从禅宗中汲取精髓,运用到书法中。黄庭坚的书法中有很多作品涉及禅宗的内容:如《诸上座帖》、《发愿文》、《明瓒诗后卷》、《此君轩诗卷》、《华严疏卷》等,可见禅宗在其书法中得到延伸和扩张。与苏轼相识并结交,是黄峪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苏轼超凡脱俗、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豁达旷放的人生态度,“高风绝尘”的审美追求及注重“神似”的创作经验无不强烈地影响着黄庭坚,为他“脱俗”美学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再次,坎坷的人生经历。长期被贬而处于颠沛流离的逆境生活,造就了黄庭坚骨鲠气坚的性格,使“脱俗”、“反俗”的精神表现在他的理论和艺术创作之中。 黄庭坚的书学思想及艺术观点深受禅宗中悟道思维的影响,在“韵”的意境下强调一种“脱俗”思想,并始终贯穿于其艺术领域中,包括审美思想、艺术理论和创作实践。显然,“脱俗”成为黄庭坚美学思想的重要核心。由此得知,他之所以在书法领域里取得令人赞叹不已的成就,其受禅宗影响的“脱俗”美学思想意义重大。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gucaoa.com/jgcgx/10830.html
- 上一篇文章: 吴镇王冕柯九思元时期书画星河中
- 下一篇文章: 可舞刀弄枪,也可舞文弄墨杜月笙的强大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