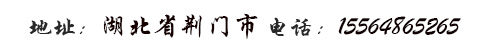他走了,留下了有关过去的集体记忆
|
白癜风医院哈尔滨哪家好 http://pf.39.net/bdfyy/bdfrczy/141015/4493986.html 晨起习字的当口,穆棱市书协主席,兄长朱孝先传来噩耗,说战争走了,于辛丑年四月初六辞世。 生命何其脆弱,在我的印象中,他才五十多岁,而且身体很能经得起折腾,长途跋涉并不在话下,怎么说走就走了。 战争本名战仁才,从妻子那边论他是我的长辈,我称其为舅。由于家里客厅大,逢年过节我便联络亲属举行家宴,只要不外出,战争也会赶过来,三代人老老少少凑在一起格外热闹。 妻子的娘家人都来自林口三道通,战争也出生在那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看过他们一众亲属的合影,那时妻子还小,看照片时感觉心都融化了,想不到那个模样清秀俊俏的小女孩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再看其他男性一律蓝色土布褂子,战争他们看上去各个是精神饱满的“愣头青”,那状态几十年都没有丝毫改变。就是这些“愣头青”,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少年在父辈的瞩望里相约走出大山,他们顺着铁道线向着城市的方向义无反顾…… 那时,我好奇怪,他怎么起了这么个不伦不类的艺名?后来了解到,他当过兵,属于行伍出身,那时部队条件异常艰苦。不过,在部队战争也没吃过苦,他被调到司令部伺候首长,多亏了一手过硬的厨艺。 他头脑活络,人机灵又勤快,很会察言观色。酱闷、清蒸、煎炸烹炒,样样通晓。但他不限于此,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又为他增添了文艺青年的色彩,在手写文稿的时代,这样的本事比厨艺更得宠。退伍之后,他进入铁路俱乐部工作,清闲之余,他又靠着心灵手巧琢磨上了摄影。 大凡聚会,他几乎成了亲属中的“笑料”,嬉笑都在脸上,喜怒从不遮掩,是个愿意表现的“话唠”又特立独行,有时候颇显得“古怪”。每次宴饮,他都会自带“筷子”,这个“怪怪”的习惯让人不解,他也懒得解释,很多时候,他就是个我行我素的存在,甚至因无所顾忌而显得不合时宜。 从跟随贾振祥先生习书,他就在亲属团聚的时候展示书法艺术。在我以为,爱好是纯粹的个人行为,不同人等之相处毕竟是短暂的交集,没有必要纠结于个人所好而影响交往的情绪。此种情况,找点共同话题,迎合迎合,敷衍敷衍便很容易一带而过,何至于“对牛弹琴”,论个高低,争个短长?若留下话柄,授人以谈资,岂不亏哉! 可战争不,他骨子里有天生的执拗,想法不需掩饰。一次,他送我一张布达拉宫照片,还装了画框,那是他去西藏拍摄的嘱咐我一定挂上。客厅的侧墙上原来挂的是朋友庆国送我的草书斗方,我不舍得摘掉。就将那幅照片放置书房自此未曾动过,没想到都过去半年了,他再来的时候自己动手摘下了书法镜框,然后再郑重其事地把他的照片端端正正地挂上去,我早已忘掉的事,他居然还记着。 因为书法,我和战争的交集,除了亲属的身份之外,又多了文化活动上的诸多往来。 当初,他没有房子,就住在铁路俱乐部,那还是单位给他的优待。年纪老大不小,又居无定所,在亲戚眼中,他显得异类。在家族中,大家通过参军、考学、打工的方式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角色转化,先后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窝。在世人的观念里,有了这样的窝才有安全感,唯独战争不一样。也许,他还要流浪,还要漂泊下去…… 直到他让我看了他的影集,对他的印象和审视才转移到另一条轨道上,而且,顺着这一条线索也许才能真正深入骨髓,撼动灵魂,从精神向度上去一遍遍捶打战争的骨肉之躯,渐露出他的真实自我。 那本摄影集叫“《为伟大而歌》——我心中的父亲母亲”。 影集是十多年前开始着手的,那时,战争离开生养自己的乡村,对于游子,远方,是静谧的风景,而渐行渐远的故乡却让他倍受煎熬。 回到久别的乡村,看到衰老的父亲母亲,一种倔犟的想法占满他思想的空间。此后,一部相机变成了他的眼睛,这眼睛在平凡和琐碎中去捕捉细节,拍下故乡,拍下父亲母亲,拍下他心中的澎湃…… 蒸馍馍,掐豆荚,拉家常,穿针引线,捣锥碾米,洗头捶背,搓衣做饭……还有烟熏火燎的土灶台,磨得铮亮的簸箕,一身残破的灯盏蜡台,连同老旧的农具和家什这些背景,加重了凝重的氛围和扑面而来的时代感,每一幅照片都蕴涵了太多的信息,蕴含了真挚质朴的情感。 所有东北农家院的生活,是那么的富有乡土气息,外溢着游子情怀,能触摸出季节的质感。朴素善良的父亲母亲举手投足间能挥洒出乡贤的风度,目光纯净如水,淡定从容而又无比坚定,虽经风雨剥蚀却不含任何杂质,那目光里能装下长满白桦的高山和流过村庄的长河,能装下世间所有悲欢愁怨…… 战争保存了一帧帧北方人的集体记忆,并将它沉淀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韵味悠远。 抓拍,战争在原生态的生活图景中留下了真实,每一个视觉的光点都是在杂乱无章的生活场景中呈现的,他从没有刻意的编排,即便是亲友聚会时的人物拍照,他也都是在别人浑然不觉中完成的,他所能做的,就是在父亲母亲的日常中留下最动情的部分。平凡纯朴的人性累加起来就变成了撼动人心的视觉效果,黑白是最纯粹的色彩,朴素、简洁、明快,并更加深刻而且富有内涵。 苦难和烦恼是等量的,父亲母亲极有耐心地消费着劳作之苦和日常烦恼,他们以苦为乐,以极强的忍耐力面对贫穷和困苦的压榨,他们用粗糙而有力的双手养活着一大家人。这双手还能化腐朽为神奇,而他们的双肩扛起的是整个家族的胆子。 父亲母亲相濡以沫,相依相伴,从生到死。没有山盟海誓,彼此的承诺都在日常的消磨中愈发坚硬无比,从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语言。 翻开影集,视线和迎面而来的过往相撞,只想哭,或多或少,那里面有我们曾经真实的自己。 一黑一白,战争用最最简洁、最明了、最大方的色彩,诠释着一正一反,一阴一阳,一明一暗,一动一静……人生世事、大道乾坤尽在其中矣。 从父亲母亲身上,战争找到了支撑点,并由此铺展开一片天地。铁路小站,少数民族建筑,他积点成线,由线而面。冥冥中,父亲母亲帮他开启了圣殿之门,沿着寂寞之途,他开始了艰难而乐在其中的朝圣之旅。 作为孤独的行者,他在意义和价值的层面一个人执意而行,越走越远。而在世俗层面,在权势和金钱大行其道的当下,他又显得渺小和无助。于是,他极尽努力,用精神的富有去填充物质的不足,他试图弥合那道深深的沟壑。 相对于摄影艺术,他的意义更在于过程,挑战极限的跋涉,完成了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甚至跨越了宗教和世俗的界限,他把历史和记忆小心翼翼地留存起来,留存在胶片上。 父辈经历的何尝不是战争经历的,父亲母亲给了他生命,乡村给了他生命,他要逆风而行,浴火而歌,留住父亲母亲的记忆,就是留下自己的足迹。留下铁路小站的影子,就是留下中国的记忆,留下天南地北的民居就是留下民族的记忆,留下中华民族文明的根脉…… 苍天有眼,它赐给勤劳有如父亲母亲一样的战争以妻女,从此,战争的身上有了丈夫的味道,有了父亲的味道,他不再漂泊。 老来得女,人生之幸!然而上苍何其残忍,幼儿园没有“毕业”的女儿,他撒手人寰,女儿再也得不到慈父的万般宠爱。今后,她的人生因为过早地失去父亲而注定缺憾。 既然选择匆匆而别,那么,曾经暖暖的父爱对于憧憬未来的孩子是不是有些残酷? 人生没有完美,缺憾就是美。一个人在精神上过于羽翼丰满,那么,在物质和世俗世界里是注定要留下太多遗憾…… 一声叹息,几多无奈? 如此,这何尝不是宿命? 所幸,有生之年,他成为文明史带着温度和思想的记录者,尽管就一点。 而能留下历史的,也必然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战争简介:原名战仁才,生于林口三道通。牡丹江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年拥有哈苏相机,取艺名“战争”。开始拍摄“牡铁人风采、牡铁《英模》和《功臣》、铁路大修人、世纪之交的《蒸汽机车》、跨世纪的爱、牡铁分局车站博览、消失的风景、我的父亲母亲”等专题。作品《穿过秋色》获黑龙江省十九届影展优秀奖,《牧歌》同时入选。 年黑白摄影画册“《为伟大而歌》——我心中的父亲母亲”入选“平遥国际摄影节”; 年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日报和中国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劳模——时代领跑者”摄影展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所拍摄牡铁分局《英模》中的“张秀琴”获一等奖,同年被中国铁路总工会授予第一批“火车头职工艺术家”; 年作品《色达喇荣佛学院僧侣住房》获“中国首届民族建筑摄影二等奖”(一等奖空缺),被“中国建筑研究会”授予“中国民族建筑事业优秀人物”,并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年在昆明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其作品——“中国民族建筑摄影组照”在会议期间的“世界本土文化展”中展出。《中国民族报》开辟“走村串寨”专栏,每期介绍一个少数民族的民居与村落,以图文并貌的形式连载了这组图片; 年5月在牡丹江市图书馆举办《我的父亲母亲》摄影展; 年5月在中国铁博物馆东郊馆举办“中国铁路实寄封收藏展”; 年10月在中国传媒大学传媒博物馆举办“中国少数民族习俗图片展”; 年11月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举办“中国少数民族居住习俗摄影展”; 年5月在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举办“蒸汽机车回顾展”。 年11月牡丹江市委宣传部授予“牡丹江最美文化工作者”; 年5月18日牡丹江市文联在党政中心报告厅举办“战仁才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年11月将全部蒸汽机车反转片无偿捐献给中国铁道出版社; 年4月将全部少数民族习俗反转片无偿捐献给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gucaoa.com/jgccd/8215.html
- 上一篇文章: 赵孟頫万寿曲,字势挺拔,笔法精美
- 下一篇文章: 台北故宫收藏的黄庭坚10件经典手札,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