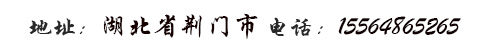她们也是女人记录战火中的女军工二
|
白癜风饮食禁忌 https://m-mip.39.net/czk/mipso_4487482.html 作者 李来梓编辑 龙山 本文选自报告文学集《绿色的群雕》,由作者授权首发。 [编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之际,全党掀起“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活动之际,回忆人民军队军需生产的发展历程,再现战火中女军工的艰难岁月,追寻她们的奋斗足迹,展示她们的革命信念,是对建党百年的特别纪念! 年初冬,我为考察红四方面军女工厂的历史,到了四川通江县的一个小镇——得汉城。这里也是红四方面军女工厂成立的地方。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得汉城成为了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维埃政府的主要后勤保障基地,红军曾在此设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电台、彭杨军事学校、保卫局、造币厂等机构。 通江得汉城旧址 年,一个白雪纷飘的季节,在红四方面军官兵衣不遮体、难以过冬的情况下,由红四方面军经理处处长郑义斋同志主持创办了女工厂。由各部队的女红军战士和当地自愿报名的几百名妇女组成的女工厂开始利用缴获来的布匹、棉花为战士缝制军衣。一座约有20多米高的山壁下,还残留着当年女军工用来染布的几个灶台。旁边的山洞里,女军工们睡过的起伏不平的石床还清晰可辨。 年纪大的老百姓还清楚地记得:女军工们如何像男人一样上山砍柴和采摘染布用的树叶野果;如何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吃着野菜、包谷和红苕而日夜不停地赶制军衣;如何剪下新来的童养媳的辫子后一同出操、爬山、唱歌、演戏;如何同男战士一起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攻,在战火弥漫的日子里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 年1月,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女工们离开了这里。从此,女工厂开始了悲壮而凄惨的历史——离开此地的多名女工,大部分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活着看到胜利的不到十分之一。死得都死去了,活着的都怎么样呢?县党史办的同志们说:“我们通江县还有两个女工厂的工人。不过她们都住在山沟里,不通汽车,需要两天的翻山越岭才能找到。而且有一个已经中风,躺在床上几年了,记忆力很差,说话语无伦次,挖不出什么东西。另外一个身体还好,经历也很特别,可以去找她谈一谈。”第二天,我怀着急切的心情登程了。经过整整两天的跋涉,找到了当年在女工厂被誉为“天仙女”的刘玉芝。 她穿着一身黑色衣服,戴一顶黑色绒帽,那布满皱纹的面容尽管憔悴消瘦,但轮廓分明的脸庞,高挑匀称的身段和宁静、柔和的眼神,仍然可以看出她年轻时的美丽和风采。 她记不住女工厂成立的时间、生产规模和领导姓名等情况。 但对她自己的经历,却记得十分清晰,并且说起来口齿利索,连细节都记得十分清楚。 图片源自电视剧《女子军魂》 “我是四川达县人,今年74岁。年,父母亲养不活我,把我送给一家姓宋的人家当童养媳。那年我才13岁。在那个家里,我受尽了欺凌,日子真难熬啊! “年10月,红军解放了达县。我看见红军队伍里有女同志,她们精神抖擞,快乐无比,使我十分羡慕。于是,我就到区苏维埃政府写了一张介绍信,报名参加了红军。 “开始我被分到通江县陈家镇小学的73师被服厂。在那里干了一个多月,就同十几名女工一起到了得汉城的女工厂。得汉城位于苦草坝的背后,四周有数丈高的陡峭石壁。全城仅有东西南北四条险路才可攀登而上,上去之后才知道有一片余亩的田地。红四方面军经理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等机关都设在这里,可热闹哩! “我们女工厂的生产场地是一个四合大院,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用石块铺成的空地,周围是一人多高的泥墙。工厂没有缝纫机,全靠手工缝制。每人每天要缝一套单军衣,衣服的款式不分男女,只是大小长短不一。 “除了做工之外,还要学习文化。我识字很快,3个月后就可以写表扬稿了。工厂里评学习标兵,每次都有我的名字。 “有一段时间,我们女工厂的女工经常到男工厂去学做衣服,学踩机器,学缝棉袄,还把前方收回来的旧衣服拿到大通河去洗,洗干净就晒到河岸石头上,然后坐在大石头上冲脚说笑,高高兴兴。一些调皮的女工还很大方地议论男工厂的工人谁长得英俊,谁的缝纫技术好……但说一会儿就都扫兴,因为大家都明白,女工的婚姻不能完全自己作主,男女婚配的方式还很陈旧。当时,也有不少女工对此有不满情绪,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是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排长撑着伞,拉着我的手去见一位领导。走进办公室,看见那个曾经给我写了几次纸条的保卫局的‘长官’,心里就明白了是婚配的事了。 “厂领导热情地给我让座、倒茶,然后深表关心地说:‘小刘啊!上次提得让你和老王结婚的事想好了吗?老王是首脑机关的干部,要不看你是工厂的‘天仙女’,人家还不同意呢?怎么样,我看这是天生一对,地配一双,你就别婆婆妈妈得了…… “我听了身上一阵燥热,满肚子的气恼一下子涌了上来,真想当着他的面大骂一通。但想到人家是上级,也就强忍住心头的火气,用沉默表示回答。 “他们见我沉默不语,又摆开官架子了:‘这是革命的需要,你不同意也这样定下来了……’听到这里,我再也坐不下去了,起身就跑出办公室,一口气跑到了男工厂,去找和我一起参加红军,当时是男工厂技术尖子的赵大明同志。 “赵大明同志也是达县人,家里也很穷,虽然没有文化,但很聪明,干什么象什么,尤其是待人十分诚恳。我在宋家当童养媳时,经常上山砍柴,下河挑水,他碰上了就要把我背上的背萎和扁担接过去。一次,他帮我砍柴,被宋家的大儿子看到了,两人就干了起来。尽管他被大他10岁的宋家大儿子打得鼻青脸肿,但他仍然像往常那样关心我。达县解放后,他报名参加了红军,第二天就通知我,还把我带到街上看文艺演出的女红军,动员我也去当红军。在他的帮助下,我偷偷地离开了宋家。到了部队后,我们都分到73师被服厂。那时,心里别提有多么高兴,就像吃了蜜糖似的。从那以后,大明便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精神力量,无论是遇到欢乐的事,还是遇到痛苦的事,我首先就去找他,而每次都从他那里得到了该得到的东西。可是这一次,他却使我失望了。当我求他同我即日举行婚礼,并说领导批评或给处分,由我一人承担的话之后,他不仅不同意,反而批评了我一顿。说什么不经组织批准就结婚是违反工厂纪律的行为。更恼火的是他说什么那个姓王的地位高,连厂领导都怕他三分,你跟着他不会吃亏的……我听了这些话,眼前全黑了,好象什么也看不见了,真想跳进大通河一死了事。但我又舍不得工厂的姐妹们,舍不得红军队伍。当时我的眼泪把衣服都湿透了,可是流不尽心中的苦闷与悲伤,一个沉重的问号始终压在心头——为什么人生中还要忍受这种奇怪的痛苦呢? “我果断而坚决地拒绝了提亲之事以后,那个‘长官’并不死心,仍然紧紧地纠缠我。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我在工厂仓库门前站岗,从天黑站到深夜两点还不见人来换岗,我好生奇怪,正在我纳闷之时,看见一个黑影朝我走来。待黑影走到跟前,我发出口令时,黑影一下子扑向我,把我死死地抱住……面对这突然发生的我从未经历的情景,我惊骇万分地叫了起来:‘抓坏人啊!‘那人不让我喊叫,一只手堵住我的口嬉笑地说:‘小刘,你别害怕,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我只是要你答应我的求亲。’这时,我才知道来人是那位姓王的。当时,我无比愤怒,用全身力气打了他一个耳光之后就瘫软在地上了。这时,他恼火了,边走边对我说:“刘玉芝,我王某不是好得罪的。” “果然,没过几天,厄运就降临了。男工厂传来了赵大明是AB党骨干分子送到了苦工大队的信息,我因和赵大明有密切关系关了7天禁闭。那时,我真伤心透了,既无法理解也不愿承认那活生生的事实,又无法渲泻心中的冤屈和羞恨。我又一次想到了死,要不是一群同甘共苦的姐妹们好心相劝,要不是与我同床的女友董桂兰日夜不离开我,要不是心里还牵挂着那个在苦工大队改造的赵大明,我早已不在人世了。 “年11月,四方面军开始向西长征。途中,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搞运输。除了缝纫工具和个人行李外,还要背供给部的光洋、金子。 “我们渡过嘉陵江后,经阆中到剑阁,便来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通过这段险路时,正赶上阴雨季节,崎岖的陡峭之路滑得像涂了光油一样,我们只好手拉着手,把身子贴着石崖一步步向前谨慎地动…… “我们来到党岭山下时,已是年春天,可这里还是风雪弥漫,冰天雪地。爬山之前,我们都喝了一大碗辣椒汤,尔后咬着牙,背着沉重的背萎,拄着棍子,一步一步向上攀登……下了雪山,大部分同志得了雪盲症,眼睛红肿,什么也看不见。但一停下来,我们仍然不停地穿针引线。许多姐妹们的手扎破了,流着血,但没有一个叫苦的。 “由于女性的生理不适应战争,比男同志遇到的困难大得多,途中找不到一张卫生纸,不少姐妹来了月经就在凉水里一蹲,让月经当时停止,所以,没有一个女工不患上妇科病。 “快到甘孜的一天夜里,张国焘的贴身交通队的几个彩号,竟然闯进我们的住所耍流氓。那夜,我刚刚进入梦乡,就隐隐约约觉得脖子上和胸前麻酥酥的感觉。不一会儿,那只温热、痉挛的手越来越沉重地在胸前乱抓。我醒了,一张丑陋的、被粗野和邪恶扭曲了的男人的脸出现在眼前,我惊觉地大叫起来:‘姐妹们,抓流氓呀!’顿时,同居室的10几个姐妹像受惊的鸟一下子翻起身来,这时,几个吓呆了的男人你撞我挤地往外跑。我操起一把裁剪,一边喊快打流氓,一边把剪子掷了过去,正好打中那个欺侮我的家伙的头。一时间,我们的剪子、尺子、棍子都成了武器,撑得他们像老鼠一样乱窜…… 图片源自电影《祁连山的回声》 “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渡过黄河,踏上了更加艰难的征程。当时,我们女工厂已由人减至余人。到了甘肃永昌后,部队供给越来越困难,为了走过河西走廊,我们白天去筹粮,晚上回来缝衣服鞋袜。任务再繁重,只要上级规定几天完成,我们就几天完成。在永昌住了两个星期,我们又转到临泽。后来敌人包围了临泽,郑义斋和秦基伟同志负责指挥总后直属部队守城。男同志守白天,我们女同志守晚上。结果苦战了三天三夜,还是失败了。突围出来的人很少,女工厂的姐妹们有的牺牲了,有的被俘,基本被敌人打散了。 “敌人把我们几十个女工押到城墙上,几个满面是血的马家兵像狼一样对我们吼叫着,还挥舞着大刀要砍下我们的头。他们的团长传令不让杀,就把我们押到野地里,要我们所有的人都脱掉衣服。第一个叫出来的女工不愿脱,敌人一枪砸在她的头上,顿时血流满面。正准备叫第二个女工脱衣时,一个传令兵跑来了,说团长同意每个人分配一个女俘。几个马家兵听后,狂欢起来。一阵狂笑后就扑向姐妹们抢开了。姐妹们气愤地叫骂着,和敌人扭打起来。但终因力不胜敌,几十名女工很快被敌人抢散了。由于我和董桂兰两人死死地抱在一起,才留在了最后。当几名马家兵朝我俩扑来时,一位姓韩的连长和一位姓叶的连副走了过来。姓叶的为了讨好连长,指着我笑嘻嘻地说:‘连长,这个女俘真漂亮,今晚就归你,剩下的这个就让我带走好了。’说完,就下令几个马家兵开始行动……我和董桂兰还是被拆散了。 “两个马家兵把我拖到姓韩的住处后刚刚出去,姓韩的就走了进来。没等他开口,我就大吼起来:‘要杀要砍随你的便,我是决不给你做老婆的。’他半晌后缓缓地说:‘我韩某人从不强人所难,对女人也一样,不主动倒向我怀中的女人我韩某决不会动情。不过,凭你的长相我还不会马上放掉你。等你考虑几天,想好之后,我们再谈怎么样呢?’说完,他把门一关,扬长而去。当时,我仿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不过惊恐与愤怒仍然笼罩着整个心灵,警惕的弦仍然绷得很紧。 “敌人把我一连关了3天。3天内,姓韩的不但没有纠缠我,还派人给我送来好吃的。当时哪有心思吃东西呢?我心里装的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早日找到红军…… “第4天,我又大吵大闹起来,摔桌子砸凳子的。姓韩的见我没有一点屈服的样子,走进来背对着我说:“既然你决意不肯随我,你走好了,我保证你安全地走出临泽城。但你是四川人,烽火连天,关山重重,你能走到哪里去呢?如果你走投无路,还可以来找我,我会欢迎你的!’他的一席话,真的还把我说得无言以对。但我心里有一个赵大明,有我无比热爱的红军队伍,我怎么能委身于一个马家兵呢?所以,我还是坚决地走出了临泽城。 “我只身一人走了7天7夜,仍然没有打听到红军的消息。 我继续向东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有一队马家兵。于是,我立即钻进路边的草丛中,等马家兵过去,我才钻出来。当时,天色已晚,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幸好碰上一位好心的大娘,把我收藏在家中,才躲过马家兵一次又一次的搜查。我见老大娘膝下无子,老伴忠厚老实,因一时找不到归宿,就答应做大娘的干女儿。 从那以后,我半年时间没有出门。因为当地话我听不懂,万一被马家兵发现,不仅自己陷进虎口,还会连累大爹大妈。所以,我听大爹大妈的话,只在家中做些针线活,对外面的事一概不管。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我临时栖身的窝被摧毁了。大爹上山打猎时摔下山谷丧命,大妈因悲痛至极,在病床上躺了半月之后就去世了。我安葬了老人,又开始流浪他乡。 图片源自电影《祁连山的回声》 “我一边讨米要饭,一边打听红军的消息。可一连数月的苦苦寻找,仍然一无所获。我只好向四川老家一步步地乞讨,因为只有那里才是我的家,那里才有我的亲人,那里才能打听到赵大明的消息。 “我历经千辛万苦,艰难地跋涉了3个多月才回到达县。当时,我已是蓬头垢面,不像人样了。 “我含辛茹苦地回到家乡,家乡给我的是什么呢?父母和3个弟妹因是红军的家属早被还乡团杀害了,我的家已不复存在了,欢迎我的是一只只嚎叫的狗子和不断向我扔石块的孩子…… “在无比惨痛而失望的情形下,我去了赵大明的家。他的家也遭到了同我家一样的灾难,也没了亲人。我只好向乡亲们打听赵大明的情况。可是,大家因怀疑我而只字不露。是大明的一位婶娘听了我的诉说之后才悄悄地把实情告诉我。她说:‘大明是红军,谁敢向你吐露他的情况呀!说完,她从箱子里取出一个包裹递给我,里面是一封写给他父母的信和他给我缝制的一套女式军衣。信是这样说的:‘我在长征中负了伤,右腿已经残废了,跟不上部队,就同救过我生命的一个回族人家的姑娘成了家。我和那家人相处很好,只是有点惦记着二老,不能尽儿子的孝道。还感到很放不下刘玉芝,也不知道她在长征中是死是活,我不能和她成家,完全是命中注定。如果她有一天回到家乡,请二老代表我祝福她幸福…… “看完那封信,我嘴已发酸,心里发胀,浑身感到出奇的寒冷,精神上产生了一种极度的恐怖,心里只是闪现着一个念头——我活不下去了,我就要死了…… “我竭力拒绝了大婶的挽留后,漫无目的地在山野里走着。 当时,映入眼帘的一座座山和一棵棵树特别冷清,特别无情,好象一个个十分讨厌我这个无家可归的女子的凶神一样,一齐挥舞着无情的鞭子,将我往地狱里猛烈地抽打…… “不知走了多少时间,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程,只知一个凄凉的月夜,我停在了一条坦荡的大江岸边,定神一看,这是通江。顿时,许多往事涌上心头……那静静流淌的江水,有我青春的热血,有我奋斗的眼泪,把自己永远落入大江,不正是自己理想的归宿吗?于是,我站在投水的位置上,仔细地环视了一遍周围冷酷的山和头顶上清凉的月以后,咬紧牙关扑了下去…… “也许阎王爷不愿收留我,也许我在人间的苦还没有吃完,我下这么大的决心却还没有死成。就在我投江之时,一个拉纤的男人把我救上岸来。这个人是通江人,当时已有30多岁了,由于家境贫寒,仍然是光棍一条。不知是他同情我,还是我同情他,我们就在一起了。从此,我们相依为命,直到现在。由于我当红军时就患下了妇科病,没有为他留下后代。尽管他想得很开,但我总感到十分内疚…… “你问我后来为什么好多年不找政府反映自己的经历,我怎么回答呢?解放那一年我见有些参加过红军的同志安排了工作,我也到县城去找过组织。那时,我还不知道红军改为解放军,看见几个穿军衣的人便连忙赶上去说:“红军同志,我是西路军女工厂的,你们能收下我吗?要不出一个证明恢复我的党籍也行啊!’他们却说:‘西路军是失败军,俘虏军,你们这些俘虏去台湾找你们的头领张国焘吧!’我听了,茫然无措,悲愤万分,眼泪也悄悄地往下直滚。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愿找政府说起那些伤心的过去了。我这个年入党的党员也就长期在党的大门之外了…… “虽然我不去找别人,但别人却不放过我。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把我叫去,问我被俘后出卖了党的什么秘密,问我是怎样从敌人的手掌心里逃出来的,是不是国民党安插的亲信……我能说什么呢?只有一言不发,任凭他们的摆布。所以,他们把我斗得死去活来,也没有得到需要的只言片语。后来左调查右调查,也没有查出我的任何历史问题。 “文化革命结束后,组织上不仅恢复了我的党籍,还按政策给我生活补助费。我真是安宁多了。随着年岁的高迈,过去的事情也淡忘了一些。所以,我平静地过几天进入黄土,也心安理得。可是生活又和我开了个玩笑,搅得我神魂颠倒,心烦意乱。那是去年夏天,县里来人接我去见一个人,你说这个人是谁?就是女工厂和我同过几年床的一起被俘后顺从了那个叶连副的董桂兰。原来她委身叶连副以后不久,便给有3个女孩的叶连副生了个儿子,成了叶连副宠爱的小老婆。解放前夕,叶连副便带着她和儿子一起逃到了台湾,现在是回来探亲的,看在过去我俩的情份上才找县里打听我的下落。我们见面后,虽然感慨万千,但我已自觉矮她半截了,人家穿的戴的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在招待所,县里的干部把她视为贵宾,杯杯浓酒朝她敬献。可我呢?和她分开后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这些罪和苦她吃过吗?要是当年和她一样向敌人屈服,不也像她一样免受生活的折磨吗?不也会有领导人向我敬酒吗?当然,在县里我是这样胡思乱想,回到家里心里也就踏实了。我想,她有她的一生,我有我的一生。我的一生是追求善良与真诚,正义与美好!虽然历经生活的艰险与困难,但我追求的东西不还是实现了许多吗?年,我的党籍得到了恢复。由于政府落实了西路军流落红军的政策,我的一生也得到了党和人民的正确评价。民政部门每月给我生活补助费,学校和工厂经常请我去讲我的故事……有了这些,我还要什么呢?” 刘老的回忆结束了,我思考的翅膀却还在飞翔……啊!我的前辈刘老,为什么岁月时光把那么多的奋斗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歌声和哭声、美好与丑恶集于你的一生呢!如果把历史喻作法官,你的坎坷生涯怎么能审判得清呢?然而,你却有那么大的存放忠与奸、良与莠的巨大矛盾体的情怀,受尽折磨而不改变执著的追求,喝尽苦水而不改变美好的人格。哪怕只有一点阳光的折射,你就尽情地发光发热,难道这就是军工战士应有的品质么? (未完待续) 邓龙您的赞赏是对三线记忆的最大支持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gucaoa.com/jgcxw/8305.html
- 上一篇文章: 端午节来了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