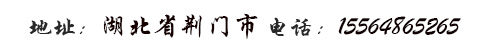草书实用与审美的冲突非草书与草
| 长沙白癜风医院 http://www.zgbdf.net/m/殷商、秦汉早期时的文字,主要还以应用为主,到汉末,随着草书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其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竞相追逐,书法的实用价值退居其次,艺术审美意识逐渐增强,尤其是杜度(操)、崔瑗、张芝等大书法家的出现,把书法推向了自觉发展的道路,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而存在。由此,出现了草书作为点画省检、提高效率的实用性与作为一门艺术的审美性之间的冲突。赵壹的《非草书》和崔瑗的《草书势》就是形成于这一时期。赵壹恃才倨傲,而又性格耿直,对社会上的邪恶丑陋现象往往直言不讳,如其《刺世疾邪赋》云:“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俊馅日识,刚克消亡。欲痔结驯,正色徒行……邪夫显进,直士幽藏……”(《后汉书赵壹传》)在经学为上的汉代,面对后学之徒对书艺小道的狂热追求,赵壹站在士大夫的立场,提出了责难。赵壹写《非草书》的目的并非见而“非”之刚刚兴起的草书,也并未否定人们对书法艺术美的追求。他在文中没有否定杜、崔、张子,而是认为他们“皆有超俗绝坡之,在“博学余暇”,的秋态中“游手于斯”,而达到“后世慕焉”的境界。他站在文人士大夫的角度担心那些“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的“当世之彦哲”和“后学之徒”对草书的狂热会本木倒置,导致“背经而趋俗”。他所反对的是那些“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唇齿常黑。……指爪摧折,见聴出血,犹不休缀”的狂怪学习草书的方式,最终非但不能把草书写好,反而“如效颦者之增丑,学步者之失节也。”从赵壹对杜、崔、张子的态度和所反对的那些狂怪学草之人,可以看出赵壹对草书艺术更加深刻的把握。他认为草书的学习要建立在“博学’的基础上,是和一个人的学养相联系的,仅仅注重对“伎艺”的追求,只能是舍本逐末,所以他在文章最后劝诫那些“言哲”和“后学之徒”说:“第以此篇研思锐精,岂若用之于彼圣经,稽历协律,推步期程,探绩钩深,幽赞神明。览天地之心,推圣人之情。析疑论之中,理俗儒之净。依正道于邪说,挤雅乐于郑声,兴至德之和睦,宏大伦之玄清。穷可以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以兹命世,永鉴后生,不以渊乎?”他把草书推到了“近乎道”的境界,强化了书法的文化性格。然而,尽管赵壹博学多识,仍未能摆脱儒家弘道思想的束缚,不能从艺术的角度,正确的看待通过书法选拔人才的社会现实。作为一位传统文人,他很难超越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所以其在论证其观点时,也恰恰从侧面反映出了问题:认为草书为实用的目的而产生。“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揚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揚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指出由于秦之末,社会动荡不安,文书频繁,为了应用的方便,把篆、隶进行草化,简化,即“删难省烦”,结果草书应运而生。并且指出好的草书并非能简简单单的学来,是需要“超俗绝世之才”的人在“博学”的基础上而达到的一种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游手于斯”。认为“草书为小道”在实用上也极为有限。他认为草书“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学习草书本就是“伎艺之细者耳”。而且就草书的功能来说,“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赵壹又从“玩物葬志”顾此失彼的角度提出“务内者必圈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们風,不暇见天。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方锐精于蛆風,乃不暇焉”,劝后之学者应树立远大志向,不能将全部精力用来学习草书,并认为即使把草书学的很好也无用武之地。当时人们的苦研草书盛况。草书在汉末作为一种时髦书体,即使草书不能使人闻达于诸侯,但从上到下的人们仍然对其钟爱,竞相学习,而且用功之勤、狂热之程度前所未有。文中描述当时书写盛况时说:“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培,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逞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判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聰出血,犹不休辍”。草书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竞相追逐,即使是忘记了吃喝、忘记了休息也不会感觉疲累;衣服上、嘴唇上常常有墨亦不会觉得难堪,纵然是“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也义无反顾。和赵壹《非草书》不同崔瑗《草书势》从草书审美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东汉中晚期,随着崔瑗《草书势》的出现,草书就逐渐从实用中脱离出来,成为人们审美的对象,进而演变成为一门艺术。其实早在甲骨文、金文时,人们也会去朝美的方向书写,只是这个时候是无意识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汉字的美,尤其是到草书,这种美变得更加纯粹,人们开始有意识的去按照美的要求去书写,渐渐使书法进入到了审美的领域。在隶书蓬勃发展时期,崔瑗拿出草书进行分析,这与草书本身的特点有着密切关联。虽然篆、隶、行、楷也能表现书法的美,但草书有它独特的优越性,草书本身符号性更强、抽象程度更高,变化也更丰富,艺术表现形式更加纯粹,更利于人们情感的宣泄。崔瑗在《草书势》中重点阐释了草书以下几种美:草书的师造化美唐代张燥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书法艺术依赖于文字,文字产生之初取象形,这就注定了书法与自然的必然联系。崔瑗的“写彼鸟迹”,蔡邑的“书肇于自然”从书论的发生之初书家就已经认识到,自然才是书法艺术的源泉,以至于后代书论无论从书法本体、风格化、价值等各个角度去阐释书法时,无不与自然界产生某种联系。张怀璀《书议》中说草书“同自然之功”“得造化之理。”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张旭喜欢写草书,喜怒哀乐等情绪,必通过草书发泄,其“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龟、草木之花实、円月、列星、风附、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自然界中的风、雨、雷、电、花、鸟、虫、鱼无不是书法取法的对象,自然界中这种不规则性恰恰成了书法的最高准则。李泽厚在《美的历程》说中国书法:“不是线条的整齐一律均衡对称的形式美,而是远为多样流动的自由美。行云流水,骨力追风,有柔有刚,方圆适度。它的每一个字、每一篇、每一幅都可以有创造、有变革甚至有个性,并不作机械的重复和僵硬的规范。”‘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草书艺术突破了种种僵硬的规范,变得更加鲜活而富有生命,它与自然界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草书的连贯、节奏、韵律之美。崔瑗讲草书时说:“状似连珠;绝而不离。”他最早记录了草书这种连贯、节奏、韵律之美。这种美首先表现在上下字之间的连贯上,“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虫蛇虫或往或还。”:’“若欲学草书……字体形势,状如龙蛇,相钩连不断……”字字之间的勾连,体现出草书独特的气势,即使是字字断开,仍气势连贯而不相离。其次,表现在单个字点画间的牵丝美。黄庭坚《山谷论书》云:“柳公权《谢紫丝級鞋帖》,笔势往来如用铁丝纠缠,诚得古人用笔意。”牵丝有轻有重,且方向不固定,常给人以独特美感。再者,草书疾如旋风,缓若绵雨的书写速度,表现出音乐的韵律美。李白《草书歌行》中“须臾扫尽数千张”、苏换《怀素上人草书歌》讲“兴来走笔如旋风”,都强调了草书书写之快的特点。李泽厚在论述书法美的原理时也说:“它(中国书法)象音乐从声音世界里提炼抽取出乐音来,依照自身的规律,独立地展开为旋律、和声一样,净化了的线条一书法美,以其挣脱和超越形体模拟的笔划后代成为所谓‘永字八法’)的自由幵展,构造出一个个一篇篇错综交织、丰富多样的纸上的音乐和舞蹈。”草书中线条的轻重、起伏、虚实等一系列变化也恰恰造就了这种韵律之美。草书的气势之美上文中已就“势”的内涵做了介绍,这里的气势仍指的是“力量”。崔瑗在论述草书势的特点时,即强调了“志在飞移;将奔未驰”的蓄势,也谈及了“畜怒怫郁,放逸生奇。……似幢郷而掮枝”的奇势,还讲到了“绝笔收势,馀綴纠结;若杜伯楗毒,看隙缘巇;腾蛇赴穴,头没尾垂”的收势。最后给人一种:“摧焉若阻卑崩崖”的不可阻挡之势。草书的“气势美”是书法美的重要范畴,张怀瑶在《书仪》中讲到草书与真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草书作品完成后,气势还像烟雾一样在作品上缓绕,虞世南《笔髓论释草》云:“草即纵心奔放……既如舞袖挥拂而萦纤,又若垂藤穋盘而绮绕……或体雄而不可抑,或势逸而不可止,纵于狂逸,不违笔意也。”‘“势”作为中国书法最早的美学范畴,历朝历代书家都为此追求不倦,而在所有字体中对草书势的追求为最。草书的法度之美。崔瑗《草书势》中最早讲到了草书书写的严谨,“是故远而望之,摧焉若阻军崩崖;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远望的是草书不可阻挡的气势,近观的是草书谨严的创作法度,即使是“一画”也“不可移”。草书自由的挥洒是人们所向往的,但这种自由需建立在严格的法度和对草书极其熟练的基础之上。“法才是最高形式的自由”。然而在我们日常草书创作中,对个性的追求经常会让我们置法度而不顾,古人的狂放癫逸并不等于胡乱妄为,明娄坚《评书》云:“素之《自叙》,虽姿态纵逸,而法度森然……”没有任何法度制约、信笔涂鸦的草书毫无艺术价值可言。当然草书的美远远不止崔瑗提及的这些,启功先生认为草书到汉末时己成为珍贵的艺术品,汉末有这种对草书美的欣赏非常难得。其实早在东汉之初,文人士大夫们就对草书产生浓厚兴趣,《汉书》中记载了陈遵善书,其书写书信被人收藏;《后汉书》中有刘睦善史书,明帝收藏其草书尺牍十首的记录。到汉末,灵帝置鸿都门学,专门培养艺术人才,对书法艺术倍加重视。关于草书的实用与审美的讨论已经历了上千年,赵壹《非草书》中的一句话:“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揭示了草书的实用和审美的冲突,书体演变的规律告诉我们草书的屯美正是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两者又存在统一的一面。从草书的产生和使用范围來看,直到魏晋时期,草书的主要功能还是起草书信或某种被迫情形下书写的文书,他的首要功能是传递信息,即以实用性为主,而并非为了审美。崔缓《草书势》说草书是:“兼功并用,爱日省力。”也说明了草书的实用价值。刘熙载《艺概书概》引欧阳修《集古录》中所讲:所谓法帖者,率皆吊哀、候病、叙瞬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在这时,字的主要功能还是为了实用,审美或欣赏还要依附于实用。由于草书难以识别、不容易掌握的特点,它的应用对象和范围又极为有限,多应用于那些熟悉草法的人群中。在草书重实用的发展过程中,审美也并未被忽略,两者可以说是一体发展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书写者重视的程度不同而已。草书原为求得简省、快速,发展到汉末时变得“难而迟”,好像草书背离原来的发展轨道,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其实就是审美的、艺术化的方向。草书进入偏重审美的领域,与它的实用性间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后来汉末“狂草”的出现更远离了实用,发展为一门纯艺术。从赵壹《非草书》中“难而迟”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草书进入审美领域后,它的法度变得更加严谨,书写的难度也明显加大,刘熙载《艺概书概》云:“崔子玉瑗)《草书势》云:‘放逸生奇,’又云‘一画不可移。’‘奇’,与‘不可移’合而一之,故难也。”极言其法度之严,从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功夫上也能看出练习草书的不易。综上所述,草书产生之初以提高书写效率为目的,主要注重的是实用性的一面。随着草书艺术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草书的美,而把它艺术化,并争相追逐,用来把玩、欣赏,尤其是发展到“狂草”而变为一门纯粹的艺术,这时主要注重的是草书审美的一面。草书的实用和审美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书写者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gucaoa.com/jgcgx/12284.html
- 上一篇文章: 被称为古老的植物黄金的一种树木,堪比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