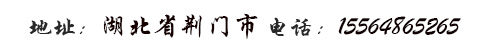ldquo孔府宴bull汉韵征文
|
人文国酿,生态原香--孔府宴酒 文/刘新铃 记忆中的稻草是温暖的,极为常见,与我们朝夕相处。它曾是那个时代农人的“救命草”,曾深入到农人的心灵。 六十年代初,鱼台“稻改”,稻草成了家里的副业。“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稻草做了蓑衣,挡住了风雨,温暖了身子。给毛窝子做草鞋垫,不管晴天雨天都能穿。北风呼啸,数九寒天,给蔬菜铺上一层稻草,是天然的“棉衣”。稻草盖的房子,冬暖夏凉(只是经不住大风大雨,需经常换新稻草)。菜市场小贩们面前总放一把稻草,鱼肉蔬菜,一两根稻草系住,从东走到西,明明白白的菜谱。稻草晒干了,垫在床铺上,那清香,那温馨,让人毫无杂念,甜美地进入梦乡。稻草会吸水,睡久了会湿,遇上晴天晒晒,可以重新垫到铺上,还是松软松软的。晒了睡,睡了晒,等到草老了,冬天也就过去了,留下的是回忆。 看到乡村,袅袅炊烟悠然,飞舞升空时,我总会记起坐在稻草前疲乏的母亲,麻利地从稻草根部折起三分之一,余下缠绕起来,打个草把扔进地锅。烘起的火光映着她黑黝黝的脸。我要母亲烧棉花秸、黄豆秸,那些揽火,饭菜好得快。母亲却说,不行,急火饭不好吃,烧鱼肉贴锅饼容易糊,耐心点,饭菜好吃。看我饿了,母亲会放一两个红薯在地锅,尚有余热的草灰中。我的饥饿,母亲的疲乏在炊烟中,无意间已经散向高远的天空和旷阔的田野。以后做事竟有了耐心。 搓绳织编织(草包)的日子最难忘。每晚,父亲饭后都会捶几把稻草,等捶熟了稻草,母亲已洗好锅碗瓢盆,我们也已完成作业。于是,在豆灯昏黄的光线下,一家四口,四张凳子,四把稻草,开始搓绳了。一边搓绳,一边往手心吐唾沫,一边听父亲老掉牙的故事。不觉间,我们身后有了一摊草绳。等到面前的一捆草要结束,我们的手掌也生疼了,口干舌燥的。看我们搓绳动作慢了,母亲会让我们先休息,而他们继续编织。白天手掌心有隐隐的血印,晚上要继续搓绳。几年下来,我家翻新了房子。母亲笑盈盈地说,以后不再要细小的搓绳了,搓得手都出血印子了。其实母亲和父亲手上的血印子是出血的,我知道。稻草让我们生活慢慢好起来,是父母亲的勤劳让我们住上了瓦房。 “不要看不起稻草,是筋骨呢。”这是外婆的话,我还记得。那时外婆把稻草混在抹熟了的黄泥中,做成一束束,围起泥瓮子、锅灶,再用稀泥涂抹,阴干,制成天然而粗糙的艺术品时说的话。柔弱的稻草也有强硬的时候。 稻草为人所用,与人生活息息相关,直至烧成草灰,还化作了好的钾肥。它在像父亲这样地道的农民眼里都是宝贝。 脱谷的稻草,扎成一把把,架成人字形,士兵似的站着,吸取自然的光和热,让风儿尽情吹拂。晒干了,父亲把他们扎成一捆捆,堆草堆。打好根基后,有高度了,母亲在下面,用叉子把一捆捆稻草举到站在草堆上的父亲。全部堆好后,还要完顶,撒上一些稻草,防止雨进去。父亲站在草堆上,满足的笑容绽开在惬意的脸上。母亲站在草堆下,乐呵呵地看着,心里似有了着落。当然,我们会更开心,因为我们可以钻草堆捉迷藏,拿开一捆草,钻进去,那捆草就当门关上。我们委屈时躲在里面,一洞一世界,静寂会让我们稚嫩的心灵得到抚慰。那一垛垛的草堆还是乡村一道道风景线呢! 可如今,稻草是令人望而生厌的。其实,机械化作用下的稻草,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稻草了,而是柔弱无力,蜷曲,散乱的草。生冷的颜色,乱糟糟地铺在田间,看得人心里涩涩的。禁烧工作严厉后,都堆在了沟渠旁,一片片乱糟糟地,污染了水源,看得人心里真不舒服。 我把好多东西演变成永久的美好回忆,留存在书本、影像中,留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比如温暖乡愁的稻草。 孔府宴酒业 长按扫码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gucaoa.com/jgcgj/4491.html
- 上一篇文章: 治疗筋膜炎的偏方大全,4个筋膜炎特效药方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